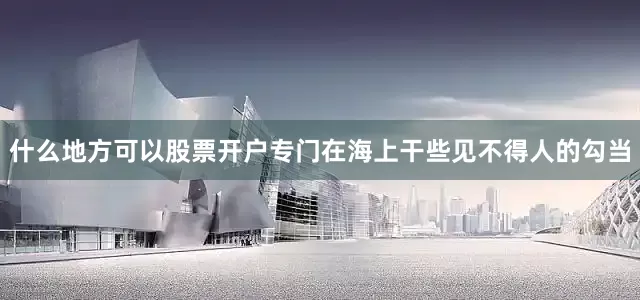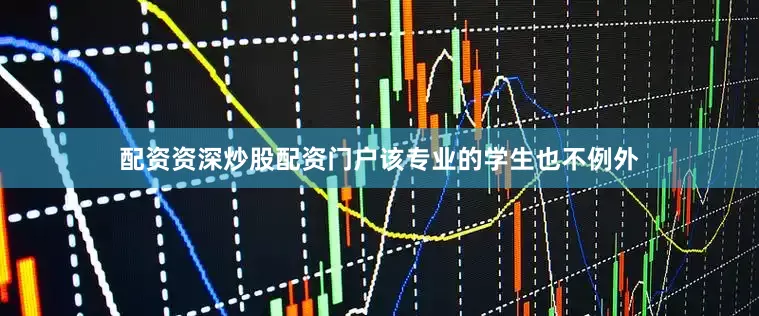八个铁帽子王里,有三家出自同一支。这支是谁的后人?礼亲王代善。更刺激的是,他本是太子,却在38岁那年因儿子“说托出走”被父亲努尔哈赤一纸废黜,连两面红旗的旗主都被夺走。一个被废太子,怎么还能让后代在清朝站成一道铁墙?一个家族起伏,背后是权力的棋局,还是制度的冷面?这些问号,值得一点点拨开。
一边是父权至上、铁面无私,一边是嫡次子、曾经的太子。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后,把正红、镶红交给代善掌管;转眼说废就废。这不是家里小打小闹,是旗权大挪移。更戏剧的是,等皇太极称帝,又把兄长代善抬到和硕礼亲王的高位。升降像坐电梯,究竟谁在操纵按钮?长子岳托又凭什么从贝勒一路到亲王,再被连番降爵,再恢复?留个扣子,后面再拆。

第一层,制度铺路。万历四十三年,八旗成形,代善掌两红旗,名正言顺。可他38岁时,因儿子“说托出走”,父子情分让位于军纪,太子位没了,旗权也交人。第二层,皇位更替。皇太极继位,代善和几个儿子表态明确,尤其长子岳托与三弟一起拥戴叔父,立了大功。皇太极建大清后,给代善补上一枚“和硕礼亲王”的重勋,算是体面归位。第三层,子嗣登场。长子岳托自幼在宫里长大,和皇太极一起被孟古哲哲抚育,21岁封和硕贝勒,22岁接掌镶红旗旗主,38岁升成亲王,却又因包庇处分降为多罗贝勒,39岁再降为固山贝子,40岁又恢复成亲王并主镶红旗,后受命为扬威大将军统八旗右翼,临行时皇太极亲送城门。可41岁天花夺命,太宗痛惜,停朝三日,追封多罗克勤郡王。次子硕托起落更狠:26岁封和硕贝勒,31岁北上攻明,曾在河北立足,却被反击,结果被革爵闲置;35岁再起,封固山贝子;40岁因僭越降为辅国公;41岁随多尔衮攻锦州,私自回营,被先革爵后又复固山贝子;44岁推举多尔衮称帝,后事败露,被罢黜宗室,沦为庶民。三子萨哈廉战功显著,后金时封和硕贝勒,天聪元年征明大捷却重伤,崇德元年(建国同年)病重离世,33岁,太宗同样停朝三日。四子瓦克达跟随皇太极、多尔衮南征北战,顺治元年封镇国公,次年晋多罗郡王,奉命平定山西,驻守平阳,军民为其建长生祠;顺治九年卒,年47,追封襄郡王。六子24岁随叔父多铎远征广西,立功;25岁授辅国公;27岁行军病逝。七子满达海早慧得离谱,7岁便奉命出师截获明军粮草;19岁征锦州;20岁封辅国公;22岁管都察院;顺治即位后23岁晋固山贝子;28岁总理六部事务;31岁夭折。八子祜塞生于努尔哈赤归天两年后,18岁封奉恩镇国公,19岁卒,子承爵;七年后追封多罗惠顺郡王,顺治十六年降为多罗贝勒,康熙元年又追封和硕亲王。老百姓看这一串官职变动,不是翻书,而是翻跟头:在平阳,百姓给瓦克达建祠,说明最直观的记忆不是头衔,而是能不能让地方安生。

看起来风浪过去了:皇太极建国,兄长受封,诸子各有爵位,家门显赫,朝堂礼数周全。可这只是表面的平静。真正的暗流,在反复的升降里。岳托的轨迹,像安上了弹簧:亲王、降贝勒、降贝子、又复亲王,再领大军,最后死于天花。制度的手,毫不手软,皇帝的手,也不掩个人喜怒。硕托更典型:从和硕贝勒,到因河北失利被打回“闲散”,再凭战功起复,转头僭越被斥,随后又因军纪问题被摘掉帽子,最后因推举多尔衮称帝而彻底出局。有人说这是铁腕,也是规矩:军功归军功,越线就挨板子。也有人叹这是政治账,不是军事账。你看,皇太极能亲送岳托出征,却也能让他关门思过;能重用,又能降级。制度像“秤”,但砝码常在君心。普通人的感受更直接。前线士兵怕的不是升降,是瘟疫与补给。天花来时,不分亲王与卒子;河北失利,带来的不是一条人事令,而是边境村子的逃荒。瓦克达在平阳留下口碑,是因为带来了秩序与粮草;多铎南征广西,六子随军立功,但27岁就倒在行军路上,家里没有庆功宴,只有一张白纸黑字的讣告。再看制度承诺的“世袭罔替”,好听,却并非铁板一块。八子祜塞身后七年被追封郡王,又在顺治十六年降为贝勒,康熙元年再追封亲王。牌子换来换去,历史像被不断修改的简报。从军功、礼制到旗务,代善这一房,繁荣背后是消耗,是拉扯,是突如其来的命运拐弯。
反转在于:最被看好的,不一定走到最后;最沉寂的,反而在后世翻红。表面看,长子岳托少年得势、统军出征,前程似锦,最终却倒在天花;次子硕托曾有锋芒,却因政治站队而被逐出宗室。反而是看起来“存在感”较弱的支系,等到康熙元年,又被追封到和硕亲王的高度。祜塞一生短得来不及施展,身后七年被加封,再被降,再被康熙抬回去,像一张被不同朝廷盖了三次章的档案。伏笔都在前面的“升降”里:建国之初,皇权要立规矩,谁出格谁挨罚;顺治朝,摄政权势如潮水,支持谁、阻止谁,决定了一家兴衰;康熙初年,需要稳定旗王体系,过去的账单就被重算。矛盾也在这里撞到一处:军功与礼制,血缘与法度,个人与家族,朝廷与八旗。每一笔晋降,都是前文铺垫的集中爆发:你以为“世袭罔替”,其实是“可上可下”;你以为“铁帽子”,其实也要看风向。权力不是一条直线,更像一口潮汐井,涨落之间,露出石阶。

然后,一切好像又归于沉寂。礼亲王的牌子还在,宗谱照写,祭祀不误。可风险并没走远。继承链条在短命与降爵中不断断裂:第五子巴喇玛24岁早逝无嗣无爵;第六子27岁行军病亡;第七子满达海31岁离世。年轻力壮的旗主相继倒下,让这个家门在最需要人手的年代屡屡“少一将”。不光是生命脆弱,路上还冒出新障碍:南北奔袭,补给难保;夺旗易,守旗难;旗主在任,既要打仗,又要理六部、工部,都察院,精力被撕裂。意见也越来越僵:有人强调纪律至上,哪怕是亲王也要按律降级;有人强调战功优先,胜则赏、败则罚,别拿礼制做外衣;还有人主张大局为重,少翻旧账。分歧越拉越大,折中越来越难。顺治九年瓦克达去世,追封襄郡王,是对功勋的承认;顺治十六年再动祜塞的身后爵,是对旧事的再审;康熙元年的回封,则是新秩序的信号。看似平稳,实则像在薄冰上行走。礼亲王这一房,光芒与裂缝并存。

直说一个结论:制度立得再漂亮,落到人身上,全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小账。说是奖惩分明,其实升了又降,降了又升,像拨号盘。说是世袭罔替,其实帽子常换,名号常调,听起来更像灵活安排。要不是后代撑起了三顶铁帽子,这段历史看上去还真不体面。赞一句严明,也是在夸一套高频调整术;夸一句公平,也是在提醒大家,公平要落在稳定上,不然就是在走钢丝。矛盾点很清楚:家法与军功同时要,情理与法理同时压,能不打架才怪。
都说这是纪律必然,有人拍手叫好:不论皇孙亲王,只要越规就挨刀。也有人摇头:帽子换得太勤,哪来长治久安?站在你这一边,觉得这是制度的硬气,还是权力的弹性?是保障秩序,还是制造不安?欢迎把你的理由摆出来,看看哪种解释更经得起推敲。

杠杆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短线炒股配资华泰期货成立于1994年3月28日
- 下一篇:没有了